為能使移民“搬得出、住得下、能致富”,巴州實施探索“生態(tài)保護和扶貧開發(fā)并舉”的移民模式,并取得顯著成效。一年多來,由于各項措施的落實,加上去年春天的降雨量較多,巴音布魯克草原生態(tài)開始轉(zhuǎn)化,部分草場牧草平均長高10厘米。
據(jù)了解,在這項工程計劃用3年時間,要從山上生態(tài)移民1400戶,6738人到農(nóng)區(qū),減畜139萬只綿羊單位。
為了生態(tài),上萬名牧民走下山
遍地牛羊,曾是牧民的期望,而真的遍地牛羊了,幸福就成了災難。
利杰望著眼前的沙丘發(fā)呆,在他的記憶中,這里曾是青草過膝、滿目蒼綠的地方,僅幾年時間,這里不但寸草不生,居然還出現(xiàn)了這道隨風移動的沙丘。他不禁想起一首常常吟唱的牧歌“草原上的風啊,輕輕搖蕩,遍地牛羊讓牧民的心兒舒暢。”
利杰已經(jīng)年過半百,他的父輩、祖輩都在這片水草豐美的草原上放過牧,他自小就生活在馬背上,搖動鞭兒,驅(qū)趕羊群,揮動套馬桿,追逐著未曾馴服的烈馬,或是坐在蒙古包中,飲一碗沁人心脾的奶茶;或是仰臥在如毯的綠草上,望著藍天,放開喉嚨,唱一曲凄婉的長調(diào)。
然而,這一切仿佛在一夜之間都變了樣。草枯了,土裸露出來,風一吹過,塵土隨風飄散,天不再湛藍,溪流不再湍急,草原在變瘦,在慢慢消失。
32歲的哈謝還在懷念幾年前的日子,蒙古包周圍的草長得茂盛,100多只羊只需在自家的蒙古包附近放放就能吃個大飽,而如今,要想讓100多只羊吃飽,北京代開發(fā)票得趕著羊群走十幾公里。
今年86歲的和靜縣原畜牧局長甫爾升回憶,從前的巴音布魯克,真是“風吹草低見牛羊”,每到6月牛馬走進去,只能看到脊背,而現(xiàn)在的6月,20厘米高的草都已鮮見了。
和靜縣縣長才仁拉去甫在他的辦公室打開多媒體播放器,大屏幕上立刻投影出巴音布魯克草原的衛(wèi)星遙感圖。隨著光標的移動,可以清晰地看到被分為大尤爾都斯和小尤爾都斯兩大牧區(qū)的巴音布魯克草原,已經(jīng)出現(xiàn)了點點黃斑,而小尤爾都斯剛被大片的黃色覆蓋。
“這就是黃沙。”才仁縣長指著大片的黃色解釋說。
“除了氣候的影響,過度放牧是草原嚴重退化的重要原因。”才仁縣長說,到小尤爾都斯親眼看到的情形,比想象的要嚴重得多。
和靜縣與15個縣市相鄰。這些縣市以及各系統(tǒng)各單位分布在巴音布魯克草原的四周,這些地方的牧民也都把牛羊趕到山上來放。最多時,山上有253.08萬只羊,而這里的理論載畜量為113.66萬只。
才仁縣長曾把這些周邊的負責人召在一起,試圖說服他們減少上山的羊群。但會議在一片爭吵中結(jié)束。“山下養(yǎng)一只羊成本60元以上,而在山上只需要不到30元,利益的驅(qū)使使得牛羊往山上走。”才仁體會到,以一縣之力無法控制山上牛羊的數(shù)量。
減畜迫在眉睫。巴州黨委和政府提出了治理的對策。來自不同層次的壓力迅速轉(zhuǎn)化成治理的動力,一系列構(gòu)想先后出臺。
輪牧、休牧、禁牧,讓疲憊的草原得以休養(yǎng)生息。每家每戶、每個單位、每個鄉(xiāng)鎮(zhèn)都限定了牲畜的數(shù)量,進山的路上設了好幾道卡,上山的牲畜,必須有身份牌,沒有身份牌的一律不得上山。
控制牲畜的數(shù)量,人多牲少,勢必會影響到一些牧民的生活質(zhì)量。牧民們沒了羊,靠什么生活?山上生活著3906戶14310名牧民,其中貧困戶1395戶4138人。2005年山上牧民人均純收入1791元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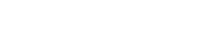
 掃碼立即溝通
掃碼立即溝通 公眾號加關注
公眾號加關注